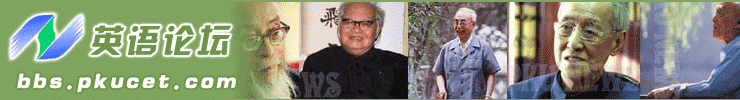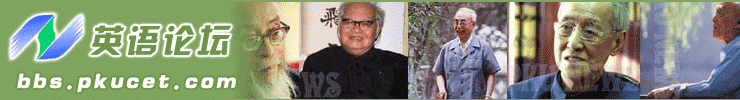翠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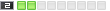

级别:论坛游侠
积分:36
经验:390
文章:33
注册:04-10-25 14:55
|
|
 |
 发表: 2005-01-12 13:42:23 人气:1772 发表: 2005-01-12 13:42:23 人气:1772    | 楼主 |
学习老板好榜样
寓言中的经济学
寓言中的经济学(自序)
自 序
日落西山,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聚集在野地里,边烧烤打回的猎物,边讲一些动物的故事。故事诙谐生动,有教诲,有讽喻。这些故事流传下来就成了寓言。阳光普照,莘莘学子们静坐在课堂听教授从最大化到边际方法讲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这些内容写成论文和专著就成了经济学。乍看起来,产生于远古、流传于民间的寓言和产生于近代、讲授于课堂上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具体生动,一个严肃抽象。但我在夜深人静读寓言和经济学时,总感到它们是相通的,在不同表述方式的背后都体现了相同的道理。寓言讲的是动物或人,反映的是人性以及做人的道理。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行为。无论在寓言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共同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寓言用原始质朴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再现了寓言中的许多简单道理。阅读各类寓言时的这点感受让我萌发了探求寓言中的经济学思想,用人们熟悉的寓言阐发经济学思想的想法。我希望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介绍一些基本经济思想,分析各种现实问题,能吸引更多人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也使人们能更容易地接近、感悟和接受经济学。这本书收录了我在阅读各种寓言中所写的65篇文章,没有什么体系,也不是系统的经济学介绍,只是有什么感悟写什么感悟,兴之所至,信手拈来而已。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从某一个寓言出发阐发一个经济学观点。用寓言来讲经济学是一种尝试,成功与否还要读者朋友们来判断。
后 记
收入本书的文章,从2003年底开始写,到2004年4月告一段落,其中大部分文章先后发表于《望东方周刊》、《南风窗》、《经济学家茶座》、《万象》、《IT经理世界》、《中国经济导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也曾被许多报刊和网站转载。发表时有些文章为了适应版面需要,由编辑做了修改,这次又恢复了其本来面貌。
在写这些文章时我阅读的主要寓言有:《伊索寓言全集》(李汝仪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版), 《拉封丹寓言诗全集》(杨松河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版),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裴家勤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版),黄瑞云、凡夫、于方选编的《经典寓言系列》(包括《中国古代寓言选》、《外国古代寓言选》、《中国20世纪寓言选》、《外国现代寓言选》四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佛本生故事选》(郭良、黄宝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在此感谢这些书的译者、编者及出版社。
在书中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曾有一些出版社表示了出版意向。最后我决定把这本书交给北大出版社,一来北大毕竟是我的母校,二来更重要的是北大出版社副社长孙晔先生、总编室主任高秀芹博士、编辑符丹和赵婕对这本书的出版、发行都提出了富有创意的设想。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梁小民
于怀柔陋室
寓言中的经济学——学习老板好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企业中,员工可以学习老板坏榜样,也可以——
学习老板好榜样
一位下岗工人以自己的经历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也努力为孩子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孩子却就是不学习。究其原因,原来是这位家长下岗后不思进取,整天在家打麻将。孩子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对麻将了如指掌,哪有学习的兴趣?
在家里,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在企业,老板就是员工的榜样。榜样有什么作用呢?《韩非子》讲过一个寓言。
邹国的国君喜欢戴有长缨的帽子,身边的人也都戴这种帽子,于是就成为一种时尚,这种长缨帽子就很贵。国君为此担心,请教臣子。臣子说,君王喜欢戴,百姓也都戴,这种帽子当然很贵。于是,邹国国君把长缨剪掉,戴没长缨的帽子出去,全国人看见国君的爱好变了,也就不戴这种帽子了。
这个寓言说明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也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榜样。在一国,国君是榜样,他的榜样比什么行政命令或道德说教都有效。在企业,只有老板能当榜样,这种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
经济学把企业家才能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并列为四种生产要素,而且,强调这四种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才能。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死的,是企业家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生产活动剧。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成败的关键。许多国家经济落后并不缺少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甚至也不缺乏技术,缺的是企业家。一个企业不成功,缺的也不是资金、人才或技术,而是企业家。离了韦尔奇就没有GE,离了郭士纳就没有IBM的大象起舞,离了比尔·盖茨也没有微软的今天。这正如国君在邹国的地位一样。
企业家被捧到了这么高的地位,他也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按传统的理论,企业家不仅是决策者和管理者,而且更应该是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在我看来,企业家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企业所有员工的榜样。
在企业中只有企业家老板能成为榜样是由于他在企业中的地位决定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企业的领导,还因为他有自然形成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来自他的权力,还来自他在领导企业前进中所形成的威望。这种威望不是别人“大树特树”产生的,而且自发形成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凭自己的本事在市场经济的夹缝中成长,从无到有,造成了一个大企业,员工能不从心里佩服甚至崇拜吗?一个国有企业家凭自己的能力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发展成一个知名企业,工人从面临下岗走向小康,员工能不给以无限的尊敬吗?老板的威信与邹国国君不同。国君是子承父业,权威来自遗传。老板是自己打天下的第一代国君,来自业绩。老板的榜样力量正来自于此。
老板的榜样力量对员工有着巨大影响,正如邹国国民模仿国君戴长缨帽子一样,员工也会模仿老板的一言一行,甚至穿着打扮。当然,这些无足轻重。老板的榜样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实施上。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也形成企业内部某种让员工工作舒心的文化气氛。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是老板个人价值观在企业的体现。因此,一个企业形成一种什么文化完全取决于老板本人,正如邹国国民爱戴什么帽子取决于国君的爱好一样。比如,现在都讲学习型企业。但是如果老板不爱学习,有时间就打麻将、跳舞,员工能形成爱学习的风气吗?如果老板没文化,念个稿子都断不成句,员工还有学文化的积极性吗?有学习之风的企业,老板必定爱学习。再如,现在许多企业都注意企业内的平等与民主气氛,这种气氛也的确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如果老板本人是萨达姆一样的独裁者,对别人不平等,独断专行,这平等与民主之风由何而来?老板不能双重人格,对别人要求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从这种意义上说,老板的素质决定了企业文化,一个素质低的老板终究是做不成大企业的。
公司治理结构是要保证企业实现制度化管理与运行。制定制度并不难,难的是制度的实施。根据我对许多企业的观察,有健全制度的企业不少,真正制度化运行的企业不多。在这些有制度而不实施的企业中,破坏制度的首先是老板本人。其他员工也会违反制度,但这无足轻重,也容易纠正。而老板“亲自”违反制度则是无人能纠正的,而且给了员工一个制度无所谓的误导。在这样的企业中,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唯老板一时的意志为转移,恐怕有再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用。
邹国国民以国君为榜样,企业的员工以老板为榜样。可以学习老板好榜样,也可以学习老板坏榜样,这完全取决于老板是一个什么榜样。老板也不会不犯错误,但记住邹国国君的寓言,有错就改也就仍然是好榜样。
寓言中的经济学——东施不可效西施
任何一种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必须牢记——
东施不可效西施
《庄子》中的东施效颦已成为一个成语,可见这个寓言流传之广了。西施是美女,一举一动都让人喜欢。她心口痛(胃病还是心脏病?) ,难受得皱起眉头,用手按着心口。这种病态美博得了人们同情。东施是丑女,总想当美女,长相是父母给的,没法换,就学西施的一举一动,连西施病态的按心口,皱眉头也学。结果“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亡走”。庄周的结论是:“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可以指许多事,例如,有了几个钱就想装贵族,落后地区经济还没上去先搞机场,无论什么体形都留明星发式,等等。不过就经济学而言,还是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
西施皱眉头美的原因是她本来就美,换言之,她皱眉头更具另一种美的前提条件是她天生丽质。如果像东施那样不具有天生丽质的前提条件,再皱眉头也没有,甚至会有相反效果。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理论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推导出来的,能否适用于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就取决于是否具有这种假设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照搬现成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已被其他国家证明是正确的,或者套用别国已有的经验--尽管这种经验在别国也是成功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
这一道理并不复杂,但人们犯错却往往就是在这些常识性道理上。比如说,在建立企业激励机制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引进在美国相当成功的股票期权制。股票期权是给企业高管在一定时期内按双方协议的价格购买一定量股票的权力。如果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提高,股票价格上升,高管就可以从股市差价中获得高收入。这种激励机制把高管的努力与企业业绩(长期盈利能力)和高管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确起了有效的激励作用。美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中有90%以上都采用了这种机制,说明这种机制是好的。
那么,这种机制适不适用于我国一些大型上市的国企呢?这就要看前提条件了。
实行股票期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完善。特别是企业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主体,有平等竞争的环境,企业业绩的好坏与高管的能力与努力密切相关。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型上市国企,实际上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其业绩好坏与高管的能力和努力相关性并不强。有些企业具有政府赋予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又无偿占有国有资源,派谁去都会有盈利。这样企业的高管获得高额股票期权收入合理吗?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国企被政府“搞”来“搞”去,一会儿要它兼并破产企业,一会儿又让它强强联合,企业没有自主权,高管都是听命于政府的有行政级别干部(正局或副局),这样的企业搞不好能怨高管吗?他们的业绩上不去,公司利润上不去,股票期权收入拿不到,能服气吗?国有企业只要姓“国”,由政府控制,就谈不上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股票期权真正是东施效颦。
实行股票期权的另一个前提是股市要完善。在这种股市上,股价由供求关系决定。当一个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提高时,其股票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种股市称为有效市场,股价变动可以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但我国的股市还远远未达到这个水平。尽管专家对股市看法不一,但政府干预过多,行为不规范,是较为一致的看法。这种股市上的股价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企业业绩,这样的股票期权又如何能有激励作用呢?
最后,股票期权制的实施要有一套完整严格的财务制度。连美国这样财务制度称得上严格的国家,都出现了安然、世通的高管为获取股票期权的收益而造假账的事,在我们这种财务制度还很不健全的国家,安然这样的事件岂不更多了?“包装上市”形象地说明了一些上市公司的作假行为,上市都可作假,“包装获取股票期权收益”不也是小菜一碟?股票期权仅仅是我们千万别学西施的一个例子。其实这些年改革中我们吃了不少东施效颦之亏,先是要学什么匈牙利模式,以后又要学韩国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其结果呢?哪个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最终要走的还是自己的中国模式。东施之错正如庄周所说:“不知颦之所以美”。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只知道人家成功,而不知成功的原因,就想“克隆”了。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在运用。如果可以简单地东施学西施,运用不就太简单了吗?走市场经济之路,保护产权,实行开放,这是经济发展的几个共同规律。这些规律让经济学家论证起来可以很复杂,但道理是简单的。各个国家走过的路都不完全一样,经济学的难点不在于了解这几个规律,而在于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运用。
历史上传说东施是丑女,丑女当然不能像西施那样去打扮或皱眉头。但东施其实也有美化自己的方法,比如穿适合自己的衣服,按自己的特点化妆,或者提高修养,以内在气质弥补外表之不足。丑并不可怕,怕的是要学美女的一举一动。同样,落后也不可怕,怕的是盲目套用发达的模式。以东施为戒,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寓言中的经济学——愚公不能移山
我们学了许多年愚公移山,也干了许多年愚公移山这类“人定胜天”的蠢事。要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求得社会发展——
愚公不能移山
《列子》中的寓言“愚公移山”,经毛主席引用,并写成人人必背的老三篇之一《愚公移山》之后,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寓言。应该说愚公那种移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也鼓励了我们奋勇向前。毛主席要我们学的也是这种精神,而不是那种具体做法。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山也并不是一种好做法。
经济学家讲实际,我们作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精神,而是要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也可以是整个社会的。要获得利益就必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那种收益小于成本的事,无论体现了多么重要的精神也不能做。愚公移山这件事最初并没有什么精神含义,只是为了出行方便。但为了出行方便而世世代代去挖太行和王屋这两座山值不值得呢?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说为了挖山所需要的镐、筐等等需要花多少钱,仅就愚公一家几代不从事任何有酬劳动,放弃的收入--机会成本--该有多少啊!搬走了山,仅仅方便了出行,又有多大收益呢?我想恐怕还是成本太大。
当然,出行方便,向外部世界开放,也许对愚公家实际收益极大。但除了移山之外也还有另外几种选择:第一,全家搬家,到交通方便的地方,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第二,购买些毛驴之类交通工具,坐毛驴外出爬山也是一种选择。第三,修路。尽管修路也不易,但总比挖整座山容易。第四,古人已会打窑洞,把这种方法用于挖隧道,固然不易,但仍比挖整座山容易。如果真把方便出行当件事做,肯定还可以想出其他替代的办法,如果再请教智叟这老头,大概还有别的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各种可行的方案中应该选择达到既定目的成本最小的方法。否则就谈不上“经济”二字了,“经济”的原意就是“节约”.
过去,我们的确是不仅学了愚公的精神,还学了愚公的做法。大寨修人造平原就有愚公的影子。人造平原花了多大成本,带来了多少收益,大概没人算过。但我想多收的那点玉米,绝对是得不偿失。而像这样的愚公做法也绝非仅仅大寨有在农业学大寨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现在转向市场经济了,但愚公这样的做法也并没有绝迹。一些地方不顾条件,不计成本修机场,搞形象工程就有点愚公的另类精神。不过,人家愚公用的却是自己的资源,当代愚公用的却是国家的资源,纳税人的钱。
愚公的做法中还有一点与现代观念相冲突之处,就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山在那里,自然有它的理由,也有它的作用。愚公移山的宣传中强调了改天换地,人定胜天,这就十分危险了。按人自己的短期利益来改造旧山河,说起来豪迈得很,但从长期看,破坏了自然界和谐的生态平衡,得到报应的还是人类自己。《列子》产生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环保思想(其实这样说还是为古人开罪,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就是环保思想),移移山也就算了,可以不追究破坏生态罪,但现在还这么做,那就是明知故犯了。寓言中没有写神仙受感动把山拿走后的结果。我想,这一地区的气候会发生变化,野生动物不复存在,愚公家出门方便了,但也没钱进城了。
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愚公精神绝对是不能实现赶追经济强国的。实现现代化需要的不仅是愚公式的苦干,还要智叟的巧干。经济学中有一个“后发优势”的概念,即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吸取先进国家的教训,更快地赶超先进国家。这种赶超效应来自后发优势。但如果只知像愚公一样每天挖山不止,还让子子孙孙都这样做,不让他们出去留学,学学人家如何解决交通问题,哪一天才能赶上人家呢?愚公还有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拒绝向别人学习,“后发”就没有“优势”,只能与先进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你还在那儿移山呢,人家的飞船都到火星了。
你挖山从理论上说绝对可以把山移走,但再挖也到不了火星。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先进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自己再努力也是愚公移山的笨做法。为什么我们在转向市场经济十余年之后才把产权改革作为中心?为什么我们长期没有解决市场秩序混乱问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惜我们学晚了。为什么当年法国的税收承包制失败了,几百年后我们还要步其后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环境破坏曾引起重大损失,我们的淮河还在污染?只像愚公那样实干苦干是不够的。巧比苦更重要,而巧只能向别人学。
愚公移山是个故事,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我解释的对不对也算一家之言吧!
寓言中的经济学——鹰永远比鸡飞得高
相关文章:
日期:2004-12-20
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经济学家,在挖苦、嘲讽、批判前辈经济学家时,千万别忘了一句俄罗斯名言——
鹰永远比鸡飞得高
读前苏联人或中国人写的经济学说史时,我经常想起列宁爱引用的一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
这个寓言的大意是,鹰在高空飞翔之后落在低矮的烘谷房上歇息,然后又向另一个烘谷房飞去。一只凤头母鸡看到了就大发感慨,鹰凭什么备受尊重,如果我愿意,也能在烘谷房之间飞来飞去,以后我们别当傻瓜,认为老鹰有着比我们显贵的门第,它们和鸡飞得一样低。鸽子对此言颇为反感就回了一句:鹰有时确实没有鸡飞得高,但鸡永远也飞不上云端!克雷洛夫的结论是,“评论天才人物,别去寻找他们的不足,而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善于理解他们所达到的高度”.
这段评论正是我读苏式或中式经济学说史时的感受。这两种经济学说史完全是一个模式,中式无非是苏式的翻版而已。
一部经济学发展史是无数先辈经济学家观察经济现象,探讨经济运行规律,实现富民强国的历史。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没有路的地方前进,他们日夜辛苦,不知疲倦地为经济学这座大厦添砖加瓦,呕心沥血。他们大胆探索这个无人知晓的领域,一点一滴发现科学真理。那些留下名的和没有留下名的前辈,那些走过弯路的勇士们,永远是经济学中的鹰。今天经济学这座辉煌大厦正是无数前辈辛勤探索的结晶。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今天显赫的科学经济学。他们不是圣人,也要受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局限。他们也提出过一些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但这正如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一样,决不能证明他们不是翱翔蓝天的鹰。我们应该以这种心态来看待前辈经济学家们的一切成果,阅读他们那字字千钧的著作。我们应该看的是他们的成就,而不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那些号称马列主义者的苏式和中式经济学史专家并不是这样。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历史的审判者自居,把前辈经济学家一个一个地推到历史的审判台上任意发落。他们写的一部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本审判记录,是一部充满无知和傲慢的批判史。在他们的笔下,经济学不是进步的,他们认为离我们越近的经济学家说的谎言越多。一部经济学史,除了到李嘉图为止的古典经济学之外,就是从庸俗到再庸俗到进一步庸俗再到现代庸俗的历史。对古典经济学也仅仅肯定现在已被遗弃的劳动价值论,而对其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则批判为“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资本主义又被作为罪恶。
连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几千年来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但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信徒者,却把探讨这种制度规律的经济学家往往斥为“资本主义辩护士”。这一根大棍打倒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经济学家。这是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以为然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认真阅读了大量前辈经济学家的著作,显然一些评论也有失公允,但还注意吸收其中合理的内容,得到了不少启示。列宁也曾强调要看前人在哪些地方有了进步。不幸的是,苏式与中式经济学史的作者都是一批到底。他们批判之荒唐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凯恩斯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摩擦失业和非自愿失业本来是要分析失业的不同原因,却被指责为“挑拨工人阶级的团结”。去读读苏共内部的肃反与屠杀,工人阶级内的不团结与凯恩斯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被歪曲了,他们的贡献被有意抹杀,而缺点则被无限放大,甚至按今天的观点来判断当时的看法。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这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深远,但在这些学说史中反复讲到的却是他反对缩短工时的工厂法的“最后一小时论”。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在西尼耳的经济学中根本不是主要内容。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是基于当时法国严重通货膨胀的状况提出的,何况强调供给的作用也并不为错。但这个观点却被歪曲,抽去其时代背景与意义,作为批判的靶子。去翻一翻这些学说史,哪一个被贴上资产阶级辩护士标签的经济学家没有受到歪曲?读这样的学说史,你能得到什么呢?
苏式中式经济学家们以为计划经济辩护为能事,但历史已证明计划经济的弊病。这样一来,这堆赞美计划经济的经济学不就成了人类后院的垃圾了吗?市场经济成为世界惟一成功的经济模式,探讨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当然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两者相比,谁是鸡,谁是鹰,还不清楚吗?
与那些为政治服务而不学无术的苏式中式经济学史的作者相比,西方经济学家还是认真做学问的。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也飞得不如鸡高,但他们是鹰,鹰永远比鸡飞得高。
|

|
|